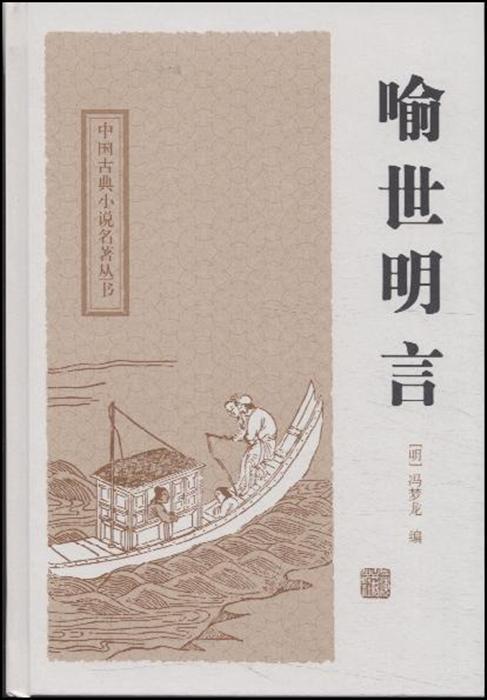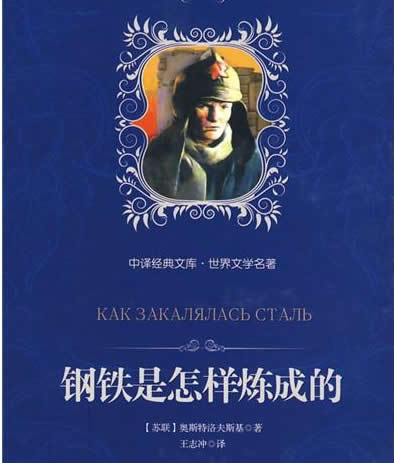- 第五章 阿拉伯海底隧道
-
当天,我就向康塞尔和尼德·兰汇报了部分谈话内容,他们立即就产生了兴趣。当我告知他们,两天后,我们就会在地中海里时,康塞尔拍起手来,而加拿大人则耸耸肩膀。
“一条海底隧道!”他喊道,“两海之间的通道!谁听说过?”
“尼德朋友,”康塞尔说,“您听说过‘鹦鹉螺号’船只吗?没有!可它确实存在着。那么,就不要轻易地耸肩膀,不要借口您没听说过,就否认那些存在着的事实。”
“我们走着瞧吧!”尼德·兰摇摇头反诘说,“总之,我还巴不得相信他的通道,相信这位船长呢,愿上帝真地把我们带回地中海。”
当天晚上,“鹦鹉螺号”船只在北纬21.3度的海面上,向阿拉伯海岸靠近。我望见了吉达港——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之间的重要商埠。我相当清晰地辨认出这座城的建筑物,以及泊在长堤边的船只和那些由于吃水度深而不得不停泊在锚地的船只。夕阳低悬在地平线上,余晖斜照着城里白色的房舍,反射得亮晃晃的。城外,几间木板房或芦苇屋,说明了这个地区住的是贝杜安人。
一会儿,吉达港消失在夜幕中,“鹦鹉螺号”船潜入了闪着微微磷光的水中。
第二天,有好几艘船迎面开来,“鹦鹉螺号”又潜入水下航行但到了中午测定方位时,海上瀚然无人,于是“鹦鹉螺号”又上浮到露出了浮标线。
此时,我坐在平台上,尼德和康塞尔陪着我。东海岸看上去女像是一大团在湿雾中时隐时现的东西。
我们倚着船舷,东拉西扯地谈起来。这时,尼德·兰用手指指着海上的一点,对我说:“教授先生,您看到那边的东西吗?”
“没有,尼德,”我回答,“您知道,我的眼睛没您好。”
“仔细看看,”尼德又说,“那边,右舷前面,在探照灯的差不多同一高度上!您没看到似乎有一团东西在蠕动吗?”
“真的,”我仔细看了之后说,“我看到了水面上好像有一个灰黑色的长物体。”
“另一艘‘鹦鹉螺号’船?”康塞尔说。
“不,”加拿大人回答,“要不就是我搞错了,要不那就是某只海底动物。”
“在红海里有鲸吗?”康塞尔问。
“有,小伙子,”我回答,“人们能偶尔见到。”
“那根本不是鲸,”尼德·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东西,说,“鲸和我是老相识,他们的样子我是不会搞错的。”
“等一等,”康塞尔说,“‘鹦鹉螺号’朝着它开去呢,一会儿我们就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了。”
确实,那灰黑色的物体距离我们仅1海里之遥。看上去就像是搁在深海里的广块巨礁。那是什么呢?我还说不上来。
“啊!它走动了!它潜水了!”尼德·兰叫起来。“见鬼!那会是什么动物呢?它没有长须鲸和抹香鲸那样分叉的尾巴,而它的鳍看上去就像是被截去一段的四肢。”
“那是……”我说。
“瞧,”加拿大人又说,“它把肚皮翻过来了,乳房朝空中挺起来了。”
“那是一条美人鱼,”康塞尔叫道,“一条真正的美人鱼,这样说先生不反对吧。”
美人鱼这个名字使我茅塞顿开。我知道这动物是属于一目海底生物,神话中半人半鱼的海怪。
“不,”我对康塞尔说,“不是美人鱼,而是一种奇怪的动物,目前在红海里仅有几只。那是一种海马。”
“人鱼目,鱼形类,单官哺乳亚纲,哺乳纲,脊椎动物支。”康塞尔回答。
康塞尔都说出来了,我就无需再说了。
尼德·兰却一直盯着那只动物。自从一看到它,他眼里便闪着贪欲的光芒。他的手似乎随时准备投出鱼叉。他好像在等待时机一到,便跳到海中攻击它的要害。
“哦!先生,”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对我说,“我还从没杀过这种东西。”
鱼叉手的全部心思都包含在这句话中。
这时,尼摩船长出现在乎台上。他看到了海马,明白了加拿大人的态度,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兰师傅,您一旦拿着鱼叉,就会手痒吗?”
“确实像您说的这样,先生。”
“某一天您从操打鱼旧业,把这只鲸类动物加到您打过的鲸鱼清单上,您是不会不乐意吧?”
“决不会不乐意。”
“那好!您可以试一试。”
“谢谢,先生。”尼德·兰回答说,眼睛都发红了。
“只是,”船长又说,“我建议您最好抓到这只动物,这对您有好处。”
“抓海马有危险吗?”尽管加拿大人耸耸肩膀,我还是问。
“是的,有时候会有危险,”船长回答说,“这种动物会调过头来反攻,把捕捉它的渔船掀翻。但对于兰师傅来说,他眼捷手快,是不用怕有这种危险的。我叮嘱他别放过这条海马,是因为人们把它视为一道美味猎物,我知道兰师傅是不会讨厌有大块的好肉的。”
“啊!”加拿大人说,“那畜生是好吃的奢品吗?”
“是的,兰师傅。它的肉是真正的好肉,非常值得称道。马来西亚人把它用于王孙公子们的餐桌上。所以人们对待这种好吃的动物就像对待它的同类海牛一样,进行大量捕捉。因此,这类动物日益稀少了。”
“那么,船长先生,”康塞尔严肃地说,“假如这头动物刚好是这一种类中的最后一头,从有利于科学的角度上讲,放过它不是更好吗?”
“可能是,”加拿大人揶揄道,“但从有利于膳食的角度上讲,最好是抓住它。”
“干吧,兰师傅,”尼莫船长回答说。
这时,船上的7个船员,像平时一样,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地走上了平台。他们中的一个人手里拿着鱼叉和一根像是猎鲸用的鱼竿。小艇被解开了,从船位上拖出来,放到了海里。6个桨手各就各位,舵手把着舵。尼德、康塞尔和我坐到了小艇的后面。
“您不来吗,船长?”我问。
“不,先生,但我祝你们得胜而归。”
6个桨手划着小艇,朝着浮在距“鹦鹉螺号”船只2海里处的海马疾驶过去。
到距离那动物几百米时,小艇就放慢速度,船桨在平静的水畔无声地划着。尼德·兰手握着鱼叉,站在小艇的前端。猎鲸的鱼叉上通常系着一条长绳,当受伤的动物拖着鱼叉逃走着,绳子便迅速松开。但眼前这根绳子长不过10来法寻,绳的另一端系着一只会漂在水面的小桶,用于指示出海马在水底的行踪。
我站起来仔细观察加拿大人的敌手。这头海马,也称儒艮,很像海牛。它长形的身体后面拖着一条长尾巴,两侧的鳍端长着真正意义上的指头。它与海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上颌两侧分另长有一根尖长的、有不同防御作用的牙齿。
尼德·兰准备捕猎的这只海马,它身形庞大,长度至少超过7米。它一动不动地,像是睡在水波上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抓它就更容易了。
小艇谨慎地向海马划近了3法寻。桨手就把桨举在半空中半蹲着,只见尼德·兰的身体稍稍向后仰,一只手熟练地投出鱼叉。
只听到“倏”的一声,突然海马不见了。尼德用力投出的鱼叉无疑只击到海水。
“他妈的!”加拿大人气愤地叫道,“我没击中。”
“不!”我说,“那动物受伤了,瞧这是它的血。不过您的鱼叉没到它身上。”
“我的鱼叉!我的鱼叉!”尼德·兰叫喊道。
这时,桨手们又开始划动桨,舵手把船指向漂浮的小桶。鱼叉捞上来后,小艇就开始搜寻那只海马。
那海马不时地浮出水面换气。它飞疾地游动着,看来受伤并有使它衰竭。艇上的人个个精神十足,小艇沿着海马的行踪穷追不舍。好几次,当小艇距海马只有几法寻,加拿大人正准备投叉,海马忽地又潜入水中躲开了,鱼叉根本无法击着它。
尼德·兰气急败坏。他用最恶毒的英语诅咒着这只不幸的动物。而我呢,虽然眼看着海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我们的计谋,我还不至于像尼德那样气得暴跳如雷。
我们毫不松懈地追捕了一个小时。我开始想,抓到它怕是很难了。这时,这只动物突然起了使它后来追悔不及的报复的坏心。它转过身,向小艇发起了攻击。
它这一举动丝毫没逃出加拿大人的眼睛。
“小心!”他说。
舵手用他那古怪的语言说了几句话,大概是提醒他的桨手要高警惕。
这时,海马追到了距小艇20英尺处,停了下来。它用它那不在嘴尖而是长在嘴上的大鼻猛地吸一口气,然后,纵身一跃,朝我们扑了过来。
小艇没能躲过它的撞击,艇身倾刻倾斜了一半,一两吨海水灌进来。但幸好舵手机敏,使受撞击的地方是小艇的侧部而不是正面,所以小艇没被撞沉。尼德·兰死死地抱着艏柱,用鱼叉往那庞然大物身上乱戳。那动物像狮子叼着一只狍子一样,用牙齿咬住船舷,把小艇衔了起来。顿时,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如果不是一直在猛击着这只畜生的加拿大人最后终于用鱼叉刺中了它的心脏,我真不知道这场冒险将如何收场。
我听到了牙齿在铁皮上发出的吱嘎声,海马不见了,鱼叉也被拖走了。但没一会儿,小桶浮出了水面,没隔一阵子,动物的尸体也跟着仰面朝天地浮了上来。小艇划了过去,把那动物拉上了艇上,然后返回“鹦鹉螺号”船上。
这只海马重5000公斤,必须用大功率滑轮才能把它拉上平台。加拿大人坚持要亲眼看看宰杀海马的所有细节,于是人们就当着他的面把海马宰了。当天晚餐时,侍者就给我端上来了几片船上厨子精心制做的海马肉。我觉得味道好极了,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一定比得上牛肉,但至少比小牛肉好吃。
第二天,2月11日,有一群燕子落在“鹦鹉螺号”船上,“鹦鹉螺号”的配膳室里又增添了一道美味猎物。这是一群埃及特有的尼罗河海燕,喙黑色,头灰色,有圆点,眼睛周围有白点,背、翅和尾巴呈浅灰色,腹部和脖子为白色,爪子是红色。同时,我们也捉到了几只颈部和头上白色带有黑点的尼罗河鸭,这是野鸟中的极品。
“鹦鹉螺号”船只的速度缓慢了下来。可以说,它是在慢悠悠地前进。我注意到,随着我们向苏伊士运河靠近,红海海水的咸味就越来越淡。
下午5点左右,我们的船处在贝特阿拉伯顶端拉斯·穆默德角的北方——拉斯·穆默德角位于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之间。
“鹦鹉螺号”开进了通向苏伊士湾的尤巴尔海峡。我清楚地望见了一座高山,在两湾之间俯视着拉斯·穆默德角。那就是奥莱伯山,摩西当年在此山顶上当面参见了上帝,神灵的光环因此不断地笼罩在那山顶上。
6点钟,“鹦鹉螺号”船只时浮时沉地通过了位于海湾里头的多尔湾。这时,我看到了海湾里的海水一片通红,正如尼摩船长观察过的一样。不久,夜幕降临,在一片沉闷的寂静中,偶尔传来了几声鹈鹕和几只夜鸟的叫声,以及怒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或远处汽轮桨叶搅动着苍闷的海湾水的吱嘎声。
从8点到9点,“鹦鹉螺号”一直保持在水下几米处行驶。根据我的测算,我们应该是离苏伊士很近。透过客厅的嵌板,我看到了被电灯光强烈地照射着的海底岩石。海峡好像变得越来越窄。
9点15分,船又回到了水面。于是,我登上平台。因为太急于想通过尼摩船长的隧道,所以我有些坐立不安。我尽量平静下来,呼吸晚上新鲜的空气。
不一会儿,在黑暗中,我看到了一丝苍白的灯火,在水气中隐隐约约地,在距我们1海里外闪烁着。
“一座漂浮的灯塔。”有人在我身旁说。
我转过身,认出是船长。
“那是苏伊士的漂浮灯火,”他又说,“我们就要到达隧道口了。”
“进去不太容易吧?”
“不容易,先生。所以我得按老习惯呆在领航舱中,亲自领航。而现在,请您下来,阿龙纳斯先生,‘鹦鹉螺号’就要进入水中了。通过阿拉伯隧道后,它才会浮出水面。”
我跟着尼摩船长走下平台。嵌板关上了,船上的储水器一充满水,船就潜入了10多米深的水中。
当我准备回房间时,船长阻住了我。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您愿意和我一起到领航舱吗?”
“求之不得。”我回答。
“那么请吧。您可以看看这次既在地下又是在海底的航行。”
尼摩船长领着我走到中央扶梯。他打开扶梯中部的那扇门。我们走过上层纵向通道,就到了在平台前端的领航舱。
这个舱每面墙宽6英尺,和密西西比河或哈德逊河上的汽轮的领航舱很相似。中间有一台垂直放置的轮机在运转着,轮机上操舵索连到“鹦鹉螺号”的后部。领航舱的板壁上装着四个透镜舷窗,以便让舵手看清楚各个方位的情况。
舱里很昏暗。但过了一会,我的眼睛就慢慢适应了。我看到了领航员,一条身强力壮的汉子,他两手扶着轮机的轮辋。在舱的外面,装在平台另一端的探照灯从船后部一直照过来,所以海里显得格外清晰。
“现在,”尼摩船长说,“让我们找找我们的通道吧。”
在领航舱里,有几条电线连接着领航舱和机器房,所以船长可以同时对“鹦鹉螺号”船发出航向和行动的指令。他按了一个金属键,轮机的速度就立刻慢了很多。
我默默地注视着此刻我们正在通过的陡峭的高石壁,这是海岸上泥沙高地的坚固地基。我们这样行驶了一个小时,只走了几米。尼摩船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悬挂在舱内的一个有两个同心圆的罗盘。船长每做一个简单手势,领航员就立刻改变“鹦鹉螺号”的航向。
我靠着左舷窗边坐了下来,观察着一些由珊瑚虫堆积成的壮观的地下建筑,以及一些植虫动物、海藻和从凹凸不平的岩石里伸舞着大爪的甲壳动物。
10点15分时,尼摩船长亲自把舵。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又黑又深的长廊。“鹦鹉螺号”船果敢地开了进去。船的两侧传来了一种不正常的声响。这是因为隧道的斜面把红海的海水灌向地中海时发出来的。尽管“鹦鹉螺号”的推进器逆流转动,尽量想放慢船前进的速度,但“鹦鹉螺号”仍随着涌流,箭一般向前冲去。
在通道狭窄的石壁上,我只看到了由于高速而摩擦出来的点点火星、笔直的痕迹和火痕。我的心嘭嘭地跳着,我用手压住胸口。
10点30分,尼摩船长松开舵,转身对我说:“地中海。”
不到20分钟,激流就涌着“鹦鹉螺号”通过了苏伊士地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