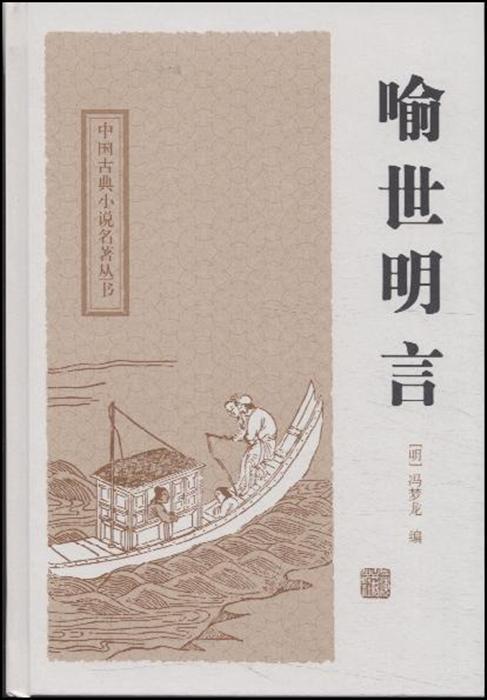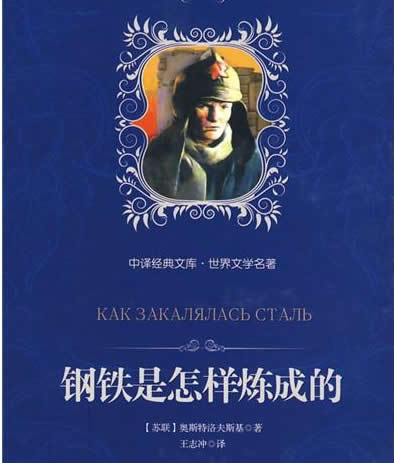- 第四章 红海
-
1月29日那天,“鹦鹉螺号”船只以每小时20里的时速在马尔代夫群岛和拉格代夫群岛间那条迷宫般的水道中行驶,锡兰岛消失在海平线下了。“鹦鹉螺号”甚至沿着吉唐岛前进。这个岛原来是珊瑚岛,1499年被华斯科·德·伽马发现的,吉唐岛是拉格代·夫群岛的19个主岛之一,位于北纬10至14.30度,东经69至50.72度之间。
从日本海出发至今,我们已经走了16220海里,也就是7500里。
第二天,1月30日,当“鹦鹉螺号”船只浮出水面时,已经一眼望不到一处陆地了。“鹦鹉螺号”行驶的方向是西北偏北,朝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的阿曼湾开去,阿曼湾是波斯海的出口处。
那明明是一条死胡同,湾内并没有出口。那么尼摩船长想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加拿大人那天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对此他大为不满。
“尼摩船长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吧,兰师傅。”
“他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加拿大人说,“可别把我们带得太远。波斯湾没有出路,如果我们进去了,还得调头按原路回来。”
“嗯!那我们就调头回来吧,兰师傅。出了波斯湾,‘鹦鹉螺号’就会从曼德海峡穿过,进入红海去的。”
“不用我说您也知道,先生,”尼德·兰说,“红海和波斯湾没啥两样,苏伊士运河还没凿通。即使凿通了,像我们这样一只神秘的船也不可能在运河的水闸中冒险。所以说,红海不是我们回欧洲要走的路。”
“您怎么想的呢?”
“我猜想,参观了阿拉伯和埃及这一带神奇的海域后,‘鹦鹉螺号’会回到印度洋,还可能会穿过莫桑比克海峡到达好望角。”
“到了好望角又怎样?”加拿大人特别强调了一下。
“那我们就会进入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大西洋。就这样!尼德朋友,您厌倦了这次海底旅行吗?对海底这些变幻莫测的奇观,您难道没有感触?至于我,我想,以后几乎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机会作这样的旅行,如里就这样地结束,我会终身遗憾的。”
“可您知道,阿龙纳斯先生,”加拿大人说,“我们被囚禁在‘鹦鹉螺号’上已经有三个月了。”
“不,尼德,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所以我不算日子,也不计时间。”
“可结果呢?”
“时候到了就会有结果的。再说,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做主,争论是没用的。诚实的尼德,如果您对我说‘逃脱的机会来了’,那我会和您讨论该怎么办的。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不妨对您直说,我不认为尼摩船长会到欧洲海去冒险的。”
通过这短短的对话,你们会发现,我对“鹦鹉螺号”着了迷了,我简直就是尼摩船长的化身。
至于尼德·兰,他自个嘀咕着结束这次谈话:“这些是好的。可依我看,哪里有束缚,哪里就没有欢乐。”
整整4天过去了,到了2月3日,“鹦鹉螺号”船只还在阿曼湾里时快时慢、时深时浅地,好像有点盲目地行驶,它仿佛对要走的路线不太确定,但它就是始终没驶过北回归线。
离开这带海域时,我们在匆忙中认识了马斯喀特城——阿曼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我欣赏了它奇特的景观,城的四周是一片黑石岩,城里建着白色的房舍和城堡。我望见了城内清真寺的圆形拱顶,塔尖优雅别致,寺前郁郁葱葱。但“鹦鹉螺号”没一下子又潜入了昏暗的水中,所以这些只是在一瞬间看到的。随后,“鹦鹉螺号”船只又沿着马哈和阿达芒一带的阿拉伯海边行驶了6海里路,沿岸山峰叠嶂起伏,偶尔有几处古代遗迹。2月5日,我们终于到了亚丁湾。亚丁湾就像一只插在曼德海峡中的漏斗,它把印度洋的海水灌进了红海。
2月6日,“鹦鹉螺号”浮出了水面,了望那处在山甲角上,与大陆仅一地峡相连的亚丁港。这一地区的海底地形和直布罗陀海峡一样,是不能通航的。1839年英国人占领这一带后,重修了这一带地区的御防工事。我远远望见了城里的八角清真寺。历史学家迪里西说过,亚丁港曾经是沿岸最富有、最有商业气息的商埠。
我深信,一旦到了这里,尼摩船长就会往回走。可是这回我又错了: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居然没这么做。
第二天,2月7日,我们的船开进了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眼泪之门”。海峡宽20海里,长仅52公里,如果“鹦鹉螺号”船只全速前进的话,不过一个小时就能穿过海峡。但因为许多从苏伊士运河到孟买、加尔各答、墨尔本、波旁、马里求斯等地的英国、法国汽轮都要从这条狭窄的通道通过,所以“鹦鹉螺号”不想浮出水面,而是小心谨慎地在水里行驶。因此,我一点也看不到岸上的情况,就连英国政府用来加强亚丁港海防的北林岛也没看到。
中午,我们的船终于浮出了红海海面。
红海,这圣经式传奇的著名湖泊,下雨不凉爽;也没有任何一条重要的河流注入。不断地过度蒸发,使它的水位以每年1米半的速度下降。这封闭的奇特湖湾,要是按一般湖泊的情况,或许早就完全干涸了。而红海现在的海平面比邻近的里海和咸海都低,后两者目前的水位已降至蒸发量和注入水量刚好相等的某一位置上。
红海长2600公里,平均宽度为240公里。在波托勒密和罗马帝国时代,她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交通要道,而现在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苏伊士铁路的部分开通使她又重新具有古时候的重要性。
这时,我不想再挖苦心思弄明白尼摩船长为什么心血来潮决定把我们带到这里了,我而且甚至完全赞同他这样做。因为,“鹦鹉螺号”船只缓缓地在水中行驶着,时而露出水面,时而为了避开水上的船只而潜入水中,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这个奇特的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观察一遍。
2月8日,凌晨,莫卡港出现了。过去,这个港城的城墙在炮声中倒塌了。港城现已沦为一片废墟,偶尔几颗苍翠的枣树遮掩着断避残坦。这座昔日重镇,曾有过6个集市,26座清真寺,城墙上筑过14座城堡,形成了长达3公里的防护区。
接着,“鹦鹉螺号”船只向非洲沿岸靠近。在这一带,海水颜色明显加深,海水像水晶般清澈。透过船上敞开的嵌板,我们可以欣赏到千姿百态的色彩绚丽的珊瑚丛,和覆盖着绿色的海藻和墨角藻的大岩石。这些多么无法形容,多么变幻多端的景观,遍布了利比亚海的暗礁和火山岛之间!不久,“鹦鹉螺号”就到达了非洲东部海岸,而在那个地方,这些枝状动物是最富有千姿万态的。德阿马海岸就在那里,那一带的海水中遍布着各种植虫动物,它们在20米深的水下组成五彩缤纷的图案。近水面的一层植虫动物受海水湿度影响小,因此色彩鲜艳。而水底的那层则色调黯淡,变化多样。
我就这样在客厅的玻璃窗前度过了多少让人留连忘返的时光!在船上探照灯的灯光中,我不知道欣赏了多少海底动植物的新种类!如伞形菌;深灰色的海葵;酷像帕那神的笛子的管状珊瑚;栖居在石珊瑚洞中,身体下部长有螺纹的这一海域的特产贝壳;还有我从没见过的成堆的珊瑚骨,即普通海绵。
海绵纲,作为水螅类的第一纲,确切地说,是由这种奇异的生物组成的。海绵不是有些博物学家所认为的一种植物,而是一种最低级的动物,则是比珊瑚更低级的水螅珊瑚虫。其动物性是不容置疑的,古人曾把它视作动物与植物之间的中介物,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是不能接受的。而我还要指出,博物学家对海绵的机体组织目前还未达成共识。有些人认为它是珊瑚骨;有些人,如麦尔一爱德华先生,则认为它是单独的个体。
海绵纲包括约300个种类。在许多海里都有海绵,甚至在一些淡水河中也存在着一类被称为河流海绵的动物。但海绵数量最多的海域当属地中海、希腊半岛和叙利亚海岸、红海等海域。这些海域中繁殖着一些质地细腻的海绵,每块价值高达150法郎,如叙利亚的金色海绵,巴巴利的硬海绵等。然而,由于受到无法逾越的苏伊士地峡的阻隔,我不可能期盼到地中海东岸考察这些植虫动物,只好满足于在红海水域里观察了。
我把康塞尔叫到身边。此时,“鹦鹉螺号”船只在平均深度为8至9米的水中,贴着东海岸那些美丽的岩石边徐徐行驶。
这一带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海绵,有带柄的、叶状的、球形的、掌形的。更具诗人气质而非学者气质的渔民们恰如其当地把它们叫做花篮、花萼、茎杆、鹿角、狮子蹄、孔雀尾、龙王手套。这些海绵珊瑚繁殖新细胞时,通过收缩运动,从纤维组织中排出细水般的半液状物质。珊瑚死后,这种物质便不再分泌,而是变质腐烂,化为氨气。这时剩下的角质或胶质纤维,就可以做成日常用的红棕色海绵,再根据其弹性、渗水性或防腐性,用于不同用途。
这些海绵珊瑚粘附在岩石、软体动物介壳甚至蛇婆茎上。它们遍布了各个小角落,有的盛开着,有的屹立着,有的像珊瑚石灰。瘿瘤一般。我告诉康塞尔说,采集海绵可以用两种办法:一是用打捞机,一是用手。后者需要雇用潜水员,但这种方法更可取,因为这样不伤及海绵珊瑚纤维,捞上来的海绵珊瑚可卖高价。
在海绵类旁边,大量繁殖着其他的植虫动物。其中以外形观的水母为主。软体动物则主要以各类枪乌贼为代表,奥尔比尼据此认为枪乌贼是红海的特产。爬虫动物以龟鳖属的条纹甲鱼为;代表,这种甲鱼可是我们餐桌上的一份卫生可口的好菜肴。
至于鱼类,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很引人注目。下面这些都是“鹦鹉螺号”船上的渔网最经常捞到的鱼:椭圆形的鳐鱼;红褐色的鳐鱼;身上有大小不等的蓝点的鳐鱼;有两道齿刺的鳐鱼;背脊银白色的白镡鱼;尾巴上有斑点的赤缉鱼;像一条2米长的衣带在水中摇摆的锦带鲜盔;和角鲨同属一个种类但完全没有牙齿的软骨鱼;长一尺半,肉峰顶部有一弯刺的驼峰牡蛎;银白色尾巴,背部略蓝,褐色的胸部嵌有灰条纹的蛇鱼;身上有金色条纹,并装饰有法国3色旗上的三种颜色,属于鲭科的光鱼;长4分米的硬鳍鱼;身上挂着7道黑色的勋带,鳍部显蓝色和黄色,鳞片金色和银色的加隆鱼;团足鱼;头部黄色的耳环豚鱼;鹦嘴鱼;鳞钝;虾虎鱼和成千上万种我们在其他海洋里都见过的普通鱼类。
2月9日,“鹦鹉螺号”船只漂浮在红海上海面宽度最宽的地方,这里西岸是苏阿金港,东岸是贡佛达港,两岸直线距离为190海里。
那天中午,尼摩船长测定了船的方位后,走上了平台,我也在那里。我心里正揣摩着:在他下去之前,起码要问一下他有什么打算。而他一看到我,就走过来,和蔼地递给我一支烟,说:
“喏!教授先生,您对红海满意吗?您有没有看够海底蕴藏的那些奇观异景,比如鱼类、植虫、海绵花圃和珊瑚丛林?您还有没有看到岸上的城市?”
“有,尼摩船长,”我回答,“把‘鹦鹉螺号’用于做这种研究是最好不过的。瞧!这是一艘智慧之舟。”
“是的,先生,这是一艘智慧的、无畏的、无可匹配的船。它不畏惧红海的风暴,也不害怕红海的海流和暗礁。”
“确实如此,”我说,“据证,红海的海上情况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它在古时候就臭名昭著了。”
“它的名声是不好,阿龙纳斯先生,希腊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就从没说过它有什么好处。史特拉宾提过,在地中海季风期间和雨季期间,在红海上行船尤其困难。阿拉伯人艾得里希曾把红海叫做科尔润湾。他叙述称,那是一片飓风肆虐的海区,水下遍布暗礁;大量的船只仅开到沙坝边就沉没了,没有人再敢斗胆到那里冒险行船;因此它的水深和海面对人来说‘一无用处’。确实,在阿里恩、阿加达尔奇和阿尔代米多尔等人的书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观点。”
“可见,”我说,“这些历史学家是没有乘坐过‘鹦鹉螺号’船只航海的。”
“没错,”船长微笑着说,“至于这个,现代人并没有比古代人进步多少。发现蒸气的动力就得花好几个世纪哪!谁知道在百年之后,人们是否还会看到第二艘‘鹦鹉螺号’呢!科学进步是缓慢的,阿龙纳斯先生。”
“是的,”我回答说,“您的船比时代提前了一个世纪,甚至可能是好几个世纪。如果这样的秘密随着它的发明者死去而死去,那该多可惜!”
尼摩船长没回答我的话。沉默了几分种后,他说:
“您想跟我淡谈古代历史学家对于红海行船的危险的看法吗?”
“没错,”我回答,“但他们的担心是不是过头点?”
“可以这样说,也不可以这样说。阿龙纳斯先生,对于一只构造结实、配备齐全、使用蒸气动力的现代船只来说,这些危险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古代船只来说,则凶多吉少。试想古代的第一批航海家,他们历险乘坐的木板小舟是用棕榈绳绑起来的,木板缝是用树脂填塞的,上面涂着海狗的油脂。他们甚至连指明方向的工具都没有,只是随着他们还不太熟悉的海流行驶。在这种条件下,海难是在所难免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在逆向季风季节,那些来往于苏伊士运河和南部海之间的汽轮再也不用惧怕海湾的狂风怒涛了。现在船长们和旅客们出发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准备祭品求神了;返航后;也不用再披花戴彩到附近的庙里谢神了。”尼摩船长回答说,好像他心里对“他的红海”深为了解。
“说得对,”我说,“我想蒸汽轮使海员们心里对神的一点感恩也荡然无存了。但是,船长,既然您似乎对这个海已经有过特别的研究,您可否告诉我它的名字的源由?”
“阿龙纳斯先生,这个问题存在着许多种解释。您想听听14世纪一个编年史家的意见吗?”
“非常想听。”
“这位幻想大师声称红海是这样得名的:以色列入通过海湾后,他们的领袖摩西便说,‘以示奇迹,让海水化为血红,叫它为红海,别无它名。’一听到摩西的声音,红海的海水便扑面而去把追赶以色列人的法老军队淹没了。”
“这是诗人的解释,尼摩船长,”我回答说,“我可不会满足于此的。我想知道您个人的看法。”
“喏。阿龙纳斯先生,按我的意见,我认为红海这个称谓应该看成是希伯莱语‘艾德隆’一词的翻译,古人之所以给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海水的特殊颜色。”
“可是到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清澈的水波,而没有任何特殊的颜色。”
“当然啦,等走到海湾尽头,您就会看到这一独特的现象的。我记得我曾看过整个红色的多尔湾,就像血湖一样。”
“那么对于这种颜色,您认为是由于某种微生海藻的存在而造成的吗?”
“是的。那是一种俗名为‘三棱藻’的有名小胚芽,它能产生出朱红色的胶粘质。一平方厘米海面就有四千个‘三棱藻’。我们到达多尔湾时,说不定您会看到的。”
“那么,尼摩船长,您不是第一次开着‘鹦鹉螺号’船来红海了?”
“不是第一次,先生。”
“那么,您前面说过关于以色列入撤军和埃及军队遇难一事,我想问问您是否在这一带水里发现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遗迹吗?”
“没有,教授先生,因为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摩西当年带着他的所有臣民走过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淤积满了泥沙,连骆驼走过时都浸不到大腿。而您知道,我的‘鹦鹉螺号’没有足够的水是走不动的。”
“那地方是……”我问。
“那地方位于苏伊士的偏上方,处在过去是深水港的海港中,而当时红海是一直延伸到咸水湖的。现在,不管这条通道是否传奇,反正以色列人是曾经从那里通过,到达希望之乡的;而法老的军队确实是在那里全军覆没的。因此,我想,在泥沙里挖掘,是能找到大量的埃及兵器和器具的。”
“显然如此,”我回答说,“但愿考古学家们有朝一日会进行挖掘。苏伊士运河凿通以后,这条地峡上就会建起一些新城市。但对于‘鹦鹉螺号’这样的船只,这是一条毫无用处的运河。”
“大概是吧,但对于全世界有用,”尼摩船长说,“古代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起红海和地中海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但他们丝毫没有想过要凿一条直通的运河,而是把尼罗河当作中转站。如果根据传说,这条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很可能是从塞索斯特利王朝就开始开凿了。有一点是能肯定的,就是公元前615年,尼哥斯领导过一条运河的开凿工程,以引导尼罗河水穿过与阿拉伯相望的埃及平原。沿该运河上溯需要4天,这条运河宽竟能容纳两只三层桨战船并排而行。接着,伊斯达斯普的儿子大流士继续了这条运河的开凿工作。大概到了蒲通雷美二世时代,这条运河才完全竣工。此后,斯达拉宾把这条运河用于航运,但由于在布巴斯特附近的出发地和红海之间的坡度不足,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航。一直到了安东尼时代,这条运河都用于商用。之后,曾被遗弃过和被淤塞过。不久,奥马哈里签发了再修通运河的命令。但到了761和762年间,阿尔一蒙塞哈里发为了阻止穆罕默德·宾·阿布达拉反政府起义军的供给,把运河彻底填平了。在远征埃及期间,你们的波拿巴将军就曾在苏伊士沙漠中发现了工程的遗址;而且,在返回阿德雅罗特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在3300年前摩西驻军的同一地方,受到海潮的袭击,差点遇准。”
“那么,船长,古代人不敢做的——开凿连接两海、把加迪斯到印度的距离缩短9000公里的运河——这一举动,现在已被德·靳斯普先生做了。而且不久,他将把非洲变成一个大岛屿。”
“是的,阿龙纳斯先生,您有理由为您的同胞骄傲。这是一位给民族赢得了比那些最伟大的船长还要多的荣誉的人!他开始干时,也像其他人一样,遇到了麻烦和懊恼,但因为他天生意志坚强,他成功了。这本是一项国际性的、足以让一位统治者千古流芳的工程,但如果把它想成只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那太可悲了!因此,光荣属于德·勒斯普先生!”
“是的,光荣属于这位伟大的公民,”我回答着,对尼摩船长刚才的强调感到非常惊奇。
“可惜的是,”他接着说,“我不能带您穿过苏伊士运河。但后天,当我们在地中海上时,您就可以看看塞得港的长堤。”
“在地中海。”我叫起来。
“是,教授先生,这让您吃惊吗?”
“让我吃惊的是想到后天我们就会到了那里。”
“真的?”
“是的,船长,尽管在您的船上这么久,我本来应该习惯于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但我还是真的很吃惊。”
“可您对什么感到吃惊呢?”
“我对‘鹦鹉螺号’船的吓人速度感到吃惊。如果‘鹦鹉螺号’后天要到达地中海,得环非洲一周并绕过好望角,那您的驾驶速度是快得吓人!”
“谁告诉您要环非洲一周的,教授先生?谁对您说要绕过好望角?”
“可是,除非‘鹦鹉螺号’在陆地上行驶,除非它从地峡上通过……”
“或是从地峡下面通过呢,阿龙纳斯先生。”
“从下面?”
“当然,”尼摩船长从容地说,“一直以来,大自然就在这咽喉之地之下,做了今天人们在地上所做的事。”
“什么!下面有通道!”
“是的,一条被我命名为阿拉伯隧道的地下通道。它在苏伊士下面,通往贝鲁斯湾。”
“但这个地峡不是只由流沙构成的吗?”
“那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是由流沙构成的。但是一到50米深处,就只会碰到那坚不可摧的岩石层。”
“您是偶然发现这条通道的吗?”我越发惊奇地问。
“靠偶然和推理,教授先生,甚至推理多于偶然。”
“船长,我在听您说话,但我的耳朵却在抵制着它所听到的东西。”
“啊!先生,‘有耳朵,却不听’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这条通道不仅存在着,我还使用过好几次。如果没有它,我今天就恐怕不会到红海这条死胡同里冒险了。”
“如果问您怎么发现这条通道,是否太唐突了?”
“先生,”船长回答说,“在彼此不分离的人之间,是不会有秘密的。”
我没理会这句话话有中话,而是等着船长的描述。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那是一个博物学家的简单推理驱使我去发现这条唯我独知的通道的。我曾经注意过,在红海和地中海里,存在着一定数量完全同类的鱼类,像蛇鱼、车鱼、纪鱼、绞车鱼、簇鱼、飞鱼。肯定了这一事实后,我思忖着,这两海之间是否存在着相通之处。如果确有通路,受两个海水位不同的影响,地下海的海流必定是从红海流入地中海。于是我在苏伊士地区捕捉了大量的鱼。在鱼尾巴上都套了一个铜圈,然后再把它们放归大海。几个月后,在叙利亚海岸边,我找到了我那些带铜圈的鱼中的几条。所以,两海之间有通路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我就和‘鹦鹉螺号’船开始寻找这条通道,终于,我发现了它,并冒险通过了它。不久,教授先生,您也将会通过我的阿拉伯隧道的。”